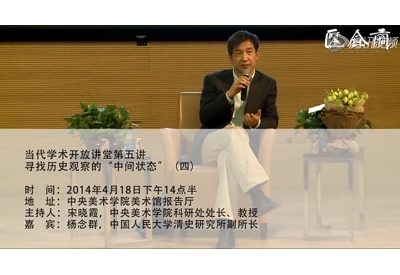4月18日下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如期迎来了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第五讲——寻找观察历史的“中间状态”,本次系列讲堂由我馆公共教育与发展部持续呈现。此次讲堂延续了前两讲对中国近代历史所进行的各方面、不同层次的讨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给出了个性化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和建议,并且在历史学的范围内自由探讨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意义、对当下中国的意义以及对建构未来的意义。

本次讲堂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杨教授系名门之后,学术主持宋晓霞教授在讲堂伊始就道明其“贵族血统”:晚清名人杨度的曾孙和梁启超的曾外孙。而杨教授本人为中国历史学界“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代表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以及《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等等。
杨教授首先借《庄子·外物》中的“得鱼忘筌”和“得意忘言”阐述了绘画艺术与历史学演变的相似之处。从现代到后现代,绘画与历史都遵循着一条反叛的线索演进。作为开场白的结束,杨教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做不到‘忘言’,而恰恰被‘言’所束缚,怎么办?

进入主要论述部分,杨教授用一条完整的线索贯穿本次讲堂的主题。首先是关于观察历史的两种极端状态:“标志性事件史”与“无事件境”。前者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内容:社会学结构分析法、内部支撑逻辑和道德判断,其精髓在于时间永远高于空间。而“无事件境”则是另一个极端,主要为人类学日常生活观察法,包含了民族志、关于历史研究单元的争论、新文化史等。克服“无事件境”的方法是建构论,因而其精髓在于以空间消解时间。
其次,杨教授阐明了历史观察呈现极端状态的弊端。有两个方面:一、标志性事件史中没有“人”,只有“物”和“势”,即标志性历史事件中具体的个人及个人价值是不存在的,只剩下“物”和“势”支撑整个事件;二、无事件境的弊端在于没有连续性价值,只承认“中断”的意义,而人类学参与观察则无法处理好“感情带入”和“理性抽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刻意追求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并以之作为观察历史的依据。在此,杨教授以“五四”运动一直以来存在两种对立解释为例来说明此立场的不妥之处。
在阐述历史观察呈现极端状态的弊端后,杨教授从个人角度出发,提出从“中间状态”观察历史。而什么又是历史的“中间状态”呢?杨教授指出,这种“中间状态”的位置是移动的而非静止的,处于“标志性事件史”与“无事件境”之间。对于这种从“中间状态”观察历史的方法,可参考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中层理论”。
接下来杨教授对如何发现和解读历史的“中间状态”给出了个人建议。首先要确定研究范围和边界。其次要寻找影响历史进程的若干要素,同时注意这些要素与历史整体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对此,杨教授举出几个重要历史研究案例:对“科举制”妖魔化的破除、从近代皇权的“人格化危机”看革命的后果等。
对于历史观察“中间状态”的叙事策略,杨教授指出对于经常使用的传统语境下的叙述词汇,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脉络里面去,尽量运用当时人们观察历史的角度,或者说叙述历史的方式来做判断,需对这些词汇在当时语境下的涵义做辨析,再考虑其在自我建构的历史叙述中的合理性和恰当性。

最后,杨教授对寻找观察历史的“中间状态”总结了两个要点,其一是避免采取某种极端“立场”;其二,观察历史不是没有“立场”,而应该包容不同的历史可能性,尽可能地采取“中立”的态度,做到不“左”不“右”。
Q&A:
1、 作为年轻人,我们怎样突破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做到自己和社会的结合?
杨:其实我们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包围之下,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一代没有这个问题,要想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话非常容易。不要看那些教科书可以了。至于怎么介入社会的问题,我觉得对社会应该保持一定的介入,但也要保持一定距离。要思考社会对你个人的关系是什么?为了观察社会,你要与它建立一种联系。
2、 您对欧立德等人的新清史,尤其是关于强调满洲特性的看法是什么?此外,现在国内的现实环境是否限制了我们对新清史的看法作出回应?
杨:这个你问对了,我们曾开了一个会专门回应新清史。新清史的优势在于把满洲的北部跟东北和西北的关系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梳理。原来我们只是强调汉化,满人吸收汉族文化,完全被汉人文化和文明所吞并,然而新清史强调的是满人自己的特性,满人跟西北、跟蒙古、东北,包括他自己的宗教,这之间有一个传承关系,而且这种传承关系也应用到了大清的整个统治里面,是有效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夸大了满人特性的作用,他们没有和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脉络里定位清朝,所以有相当大的片面性。但是我想这些美国的新清史派也有其功利考虑,因为这里面带有政治关怀和背后的话语。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蒙族、包括维吾尔族都有独立的合法性,因为这是在一个所谓的新清史的框架下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在解构中国,解构大一统的话语。
其次,我认为政治环境并没有阻碍新清史的研究,他们在美国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都比较强调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到了中国又不强调了。我的一个看法是要尽量排除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还是把其放到当时的历史脉络里去看。
3、 您刚才提到了保留皇帝这个问题,您指的保留皇帝,是当时的环境下最好的、以一种缓和的、君主立宪制这样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但最终还是走向了革命。抛开官方的历史必然性的说法,您觉得历史当中偶然性的因素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杨:关于保留皇帝的问题,实行君主立宪,我当然和我的祖宗基本上观点一致。放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下,如果皇帝仅仅作为象征符号存在,底下进行立宪系列的操作,这是中国走向一个更民主、更法制的最佳途径,甚至北洋时期都有这个机会。现在把北洋污名化、妖魔化,其实北洋那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经济也不错,整个系统良性运转,外交也不错。我们说那个时候丧权辱国,其实那个时候在外交上建立起了非常合理的东西。
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它们是相对应的,革命不一定是必然的,但是革命确实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偶然发生的里面侵染了各式各样的非偶然的因素,一个偶然的因素导致了革命的发生。我只能这样回答你,虽然这个回答比较狡猾,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历史学本来就是狡猾人的学问。
周颖南/整理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出版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下简称“CAFAM”),愿意将本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包括美术馆会员活动)的涉及本人的图像、照片、文字、著作、活动成果(如参与工作坊创作的作品)提交中央美术学院用作发表、出版。中央美术学院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它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资料库》等相关资料、文献、档案机构和平台,在中央美术学院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相关“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出版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下简称“CAFAM”),愿意将本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包括美术馆会员活动)的涉及本人的图像、照片、文字、著作、活动成果(如参与工作坊创作的作品)提交中央美术学院用作发表、出版。中央美术学院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它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资料库》等相关资料、文献、档案机构和平台,在中央美术学院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相关“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出版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下简称“CAFAM”),愿意将本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包括美术馆会员活动)的涉及本人的图像、照片、文字、著作、活动成果(如参与工作坊创作的作品)提交中央美术学院用作发表、出版。中央美术学院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它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资料库》等相关资料、文献、档案机构和平台,在中央美术学院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相关“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