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8日下午14::30,由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美术馆、人文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协会协办,刘小东、王璜生、尹吉男任总策划,宋晓霞任学术主持的“当代学术开放讲堂”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了本学期的首场讲座。就在前不久的文化部全国美术馆2013-2014年度优秀项目评选中,“当代学术开放讲堂”被评为优秀公共教育项目。
这一讲的主题为“电影书写”。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与清华大学陈永国教授就中国(华语电影),以内在的政治经济学视点,从西方批评理论到中国个体的生命体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与我院师生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
学术主持宋晓霞教授开题即提出“我们如何介入、参与电影书写”的问题。她说,在今天越来越多艺术家以影像为媒介进行创作之际,关于电影,已经不是被我们 “隔岸观火”地在艺术门类下旁观的一个学科,而是与我们美术创作息息相关的艺术活动。戴锦华教授的电影书写,首先不是回答电影研究的问题,而是去描述、勾勒她所面对的激变中的社会,以及她自己在激变中的生命经验中,如何呈现和批判她自己的,同时也是时代的情感结构。在社会关注和个人体验上,戴老师与我们艺术家是相通的。那么今天,我们应该从什么视角来参与这场关于电影的讨论?
这场关于“电影书写”的对话主要分为四个小节。首先,陈永国就戴锦华的新书提出了一个颇具电影现场感的哲学问题:假设波德莱尔有一天想和本雅明进行一次私密谈话,却遭到了七个小老头和小老太太的偷听,他们还带着录音机、摄像机等电子设备。那么谈话该如何进行?如果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来到北京的高校,他们会乞讨吗?假如在私密的谈话中还有中国三个著名的电影导演,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个谈话场景?
戴锦华将这个哲学问题以“形而下滑”的方式定义为他者对于自我的意义以及主体的构成问题。现代人自认的主体意志永远是参照在他人的自我想象和他者的在场之间完成的。这场私密的谈话由于观众的在场被解构和改变,再加上一系列的媒介工具,私密性彻底消失了。陈永国所说的这种场景放在今天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类似于知识分子的言说——即使以独白、自我娱乐的形式进行,每种书写也无法避免观看者和记录者的存在,它具有某种天然的公众性。至于三位有名的中国电影导演,他们肯定对乞讨的本雅明和波德莱尔视而不见,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悲哀,也是电影的悲哀。
对话的第二个部分围绕上世纪80至90年代在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谈论了西方的东方主义和电影中颠覆性的政治策略。以张艺谋的作品《红高粱》为例,陈永国问戴锦华为什么张的此类电影会在西方引起如此大的影响,而国内又有多少观众能理解电影中对意识形态的挖掘。戴锦华认为张艺谋的走红并非偶然,他非常有意识地以国际电影节为目标去结构他的电影,这又正好符合了整个欧洲对非西方国家电影的一种期待。但张的电影弄混了主体和客体,他用西方主体式的视角看待中国,是一种自我东方化。
接着,二位主讲人针对当今中国电影发表了各自看法。陈永国将思想和民族性上的缺失以及自我与他者的混淆视作现在中国电影一边票房高涨,另一边则恶评如潮的现象的本质原因。戴锦华补充说这是被裹挟进现代化进程的非西方国家的普遍问题。电影属于工业体制和商业体制,这使其个人化的实践可能性很小。这不是中国电影缺失的有效解答。中国电影当不起这样的责任,这是整个文化的问题。
对话的最后一部分集中于历史的创伤及其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以电影《南京!南京!》为例,陈永国认为其在人性的揭示上远不如西方在处理同类题材上来得深刻。戴锦华指出陈永国的观影体验是我们作为已迷失了的自我和主体的共同情境的隐喻。导演过度刻画了人性,但却只表现了战争之内的景象,战争之外的东西却没有出现。所以,中国人内心的创伤一直不能被有效地治疗,这也导致我们时至今日仍然不能健康地面对中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文化方面的交流。
最后,戴锦华指出,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的创伤是深刻、多端的,但我们通常都是不及悲悼就急速前行。我们需要悲悼,忘掉过去,才能前行。二十世纪对今天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它的背叛,这种背叛是反抗性的、对社会宿命的背叛,是一种不认命。今天,之所以社会带给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背叛的能力,即使是忠诚也是非常疲惫的。陈永国接续道,当下所记录的历史、记忆其实也是一种反历史、反记忆,它的目标就是为了当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为了更好地活着。碎片化、非线性的历史对我们是有益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
Q&A
1、 大众电影文化和关于具有特殊性历史的电影文化是否有共通点?
戴:电影的尴尬之处就在于,虽然它是最伟大的艺术样式之一,但也无法避免它的铜臭和机油味,因为它属于工业体系。造成《南京!南京!》这样的电影的问题不仅在于娱乐化,它并非试图追逐市场或取宠观众。而娱乐性也不会干预到历史呈现。《智取威虎山》这部电影非常好玩,是一个极端特殊的文本,携带着文革记忆,京剧改革、现代性等等历史描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观的样本。徐克只不过用它的改写给出了一个回声。香港导演改编的红色经典,是一个投名状,以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的历史被飞地化。
2、中国的电影很愿意谈论过去和今天,但为什么不愿意描述未来?
戴:五四以来的传统就是求新,但我们虽然不断畅想未来,但对未来的想象却是建立在乐观之上,而不是畅想、构想本身。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未来学,在知识生产体系上也没有,只有科幻。六十年代中国有一部科幻电影,叫《小太阳》,但还没出世就被毙了,因为显见的政治禁忌。其实这部电影不比同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差。除此之外,科学是我们最大的神话之一,而科幻的基本特点是反科学,是对科学的反叛。但是这个东西正在被逆转,比如《星际穿越》这部电影中所揭示的种种科幻与科学接轨的可能性。而且目前中国的思路也正在与世界接轨,比如《三体》的成功。
陈: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太重视历史的民族,不断地拯救历史以至于丧失了历史。同时,政府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计划也从政治上限定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力。
3、 我们如何去唾弃像《南京!南京!》这样票房热卖,却历史观有问题的电影?影评到底起了多少积极作用?
戴:整个中国的电影市场和文化生态当中,影评都没能进入一个有机环节,自身处于断裂、缺席的状态。中国的电影市场极端怪诞,越看越骂,越骂越看。而今年全球电影的普遍现象也是不烂不卖。这种遭遇指示了媒体的转型、数码转型。它绝不仅仅是媒介的改变,而是文化生态的改变。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结构转变与数码转型同步发生。影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生存?回到《南京!南京!》,影评的缺席不是最重要的。这部电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权威机构的肯定,还纳入了爱国电影的系列。如果以这样的影片进行历史教育的话,这和日本最右翼的教课书有什么区别?
文/周颖南
图/董慧萍、和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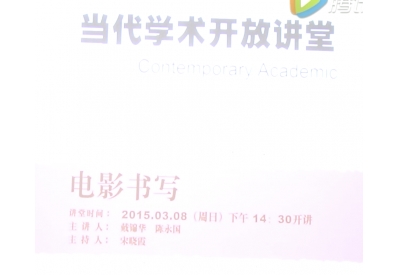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出版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下简称“CAFAM”),愿意将本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包括美术馆会员活动)的涉及本人的图像、照片、文字、著作、活动成果(如参与工作坊创作的作品)提交中央美术学院用作发表、出版。中央美术学院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它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资料库》等相关资料、文献、档案机构和平台,在中央美术学院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相关“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出版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下简称“CAFAM”),愿意将本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包括美术馆会员活动)的涉及本人的图像、照片、文字、著作、活动成果(如参与工作坊创作的作品)提交中央美术学院用作发表、出版。中央美术学院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它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资料库》等相关资料、文献、档案机构和平台,在中央美术学院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相关“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出版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同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以下简称“CAFAM”),愿意将本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组织的公益性活动(包括美术馆会员活动)的涉及本人的图像、照片、文字、著作、活动成果(如参与工作坊创作的作品)提交中央美术学院用作发表、出版。中央美术学院可以以电子、网络及其它数字媒体形式公开出版,并同意编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央美术学院资料库》《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资料库》等相关资料、文献、档案机构和平台,在中央美术学院中使用和在互联网上传播,同意按相关“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活动安全免责协议书
第一条
本次活动公平公正、自愿参加与退出、风险与责任自负的原则。但活动有风险,参加者应有必要的风险意识。
第二条
参加本次活动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遵循道德和社会公德规范,并应该具备以人为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
第三条
参加本次活动人员应该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1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必须在成年人的陪同下参观。
第四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负。鼓励参加者自行购买人身安全保险。活动中一旦出现事故,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但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参加活动的成员应当积极主动的组织实施救援工作,但对事故本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参加本次活动者的人身安全不负有民事及相关连带责任。
第五条
参加活动者在此次活动期间应主动遵守美术馆活动秩序、维护美术馆场地及展示、展览、馆藏艺术作品及衍生品的安全。活动中一旦因个人原因造成美术馆场地、空间、艺术品、衍生品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破坏。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应由参与活动者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组织规定进行协商和赔偿。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第六条
参与活动者在参与活动时应当在美术馆工作人员及活动导师、教师指导下进行,并正确的使用活动中所涉及到的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若参与者因个人原因在使用相应绘画工具、创作材料及配套设备、设施造成个人受伤、伤害他人及造成相应工具、材料、设备或设施的故障或损坏。参与活动者应当承当相应的全部责任,并主动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活动中任何非事故当事人及美术馆将不承担人身事故的任何责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肖像权许可使用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为明确肖像许可方(甲方)和使用方(乙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就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的使用达成如下一致协议:
一、 一般约定
(1)、甲方为本协议中的肖像权人,自愿将自己的肖像权许可乙方作符合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用途。
(2)、乙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是一所具有标志性、专业性、国际化的现代公共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时代同行,努力塑造一个开放、自由、学术的空间氛围,竭诚与各单位、企业、机构、艺术家和观众进行良好互动。以学院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策划国际、国内多视角、多领域的展览、论坛及公共教育活动,为美院师生、中外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的平台。作为一家公益性单位,其开展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学术性和公益性为主。
(3)、乙方为甲方拍摄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所有公教活动。
二、拍摄内容、使用形式、使用地域范围
(1)、拍摄内容 乙方拍摄的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内容包括: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②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3由中央美术学院公共教育部策划或执行的一切活动。
(2)、使用形式 用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出版、销售附带光盘及宣传资料。
(3)、使用地域范围
适用地域范围包括国内和国外。
使用肖像的媒介限于不损害甲方肖像权的任何媒介(如杂志、网络等)。
三、肖像权使用期限
永久使用。
四、许可使用费用
带有甲方肖像作品的拍摄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于拍摄完带有甲方肖像的作品无需支付甲方任何费用。
附则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可作为本协议的补充协议,并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勾选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包括纸质档和电子档,纸质档—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活动参与者意味着接受并承担本协议的全部义务,未同意者意味着放弃参加此次活动的权利。凡参加这次活动前,必须事先与自己的家属沟通,取得家属同意,同时知晓并同意本免责声明。参加者签名/勾选后,视作其家属也已知晓并同意。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条款,并且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