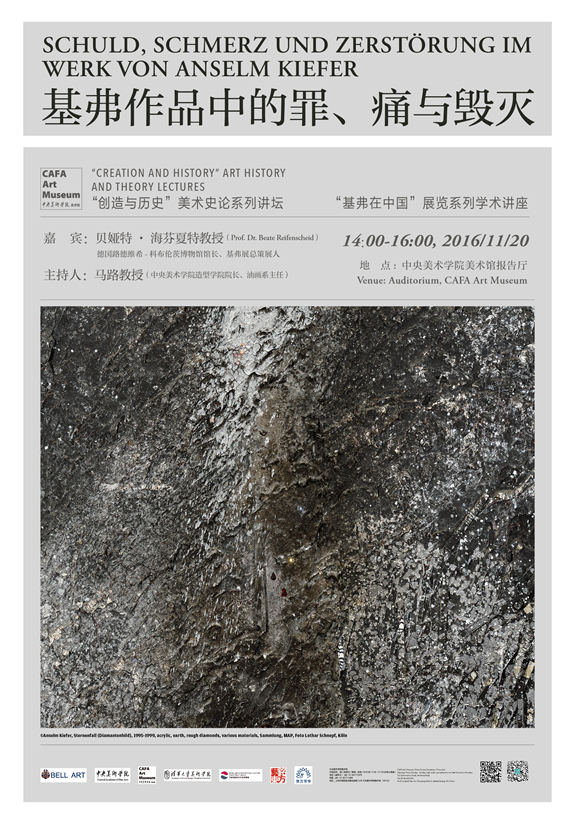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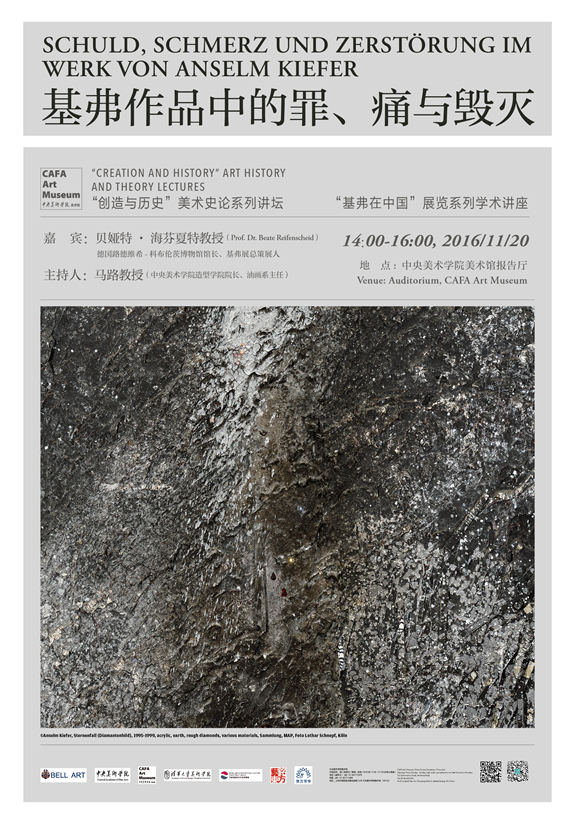
题目:基弗“在中国”展览学术讲座:基弗作品中的罪、痛与毁灭
时间:2016年11月20日下午14:00
【讲座简介】
风景不再是单纯的风景,物也不再是纯粹的物。在艺术家基弗的画笔下,作品成为历史、传说、神话、政治等等的载体。基弗身负着道德使命。在海芬夏特教授的讲述中,您将了解到基弗如何画出毁灭、罪责与尘世之痛。
【主讲嘉宾介绍】
贝娅特· 海芬夏特,生于1961年,在波鸿市鲁尔大学主修艺术史、德语文学,新闻以及传播学。之后,在马德里的康普斯顿大学留学,于1985年获得艺术史硕士学位。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在萨尔布吕肯的萨尔州立博物馆见习2年,其后成为萨尔州立博物馆的版画和绘画部主管以及公共事务部门负责人。随后数年中,她先后在萨尔州大学、希尔德斯海姆大学以及科布伦茨-兰道大学担任讲师。自1997年至今,她在科布伦茨的德意志骑士之家的路德维希博物馆担任馆长。自2004年起,她开始同中国的博物馆以及艺术院校密切合作。2010年,她成为德国ICOM董事会成员。2013年荣获科布伦茨-兰道大学名誉教授头衔。 2017年元月起,她将成为德国ICOM主席。
【讲座内容】
几乎没有哪个艺术家能够像基弗这样塑造自己的一个神话,他以他的知识以及整个知识系统的这样一个传承来塑造着有关自我的图像学,尽管他的很多内容已经溢出了这个时代所能够浅显理解的。应该说基弗他自己创造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有非常多的分支,还有一些交互影响的观点,这些非常细腻、交错的东西构成了一种多重的和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他的作品和创作当中所引用的东西:比如说像是德国一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甚至也包括一些犄角旮旯的像罗伯特·弗来德或者是赫劣布里科夫这些诗人的作品,还有像神秘浪漫主义,代表人是荷尔德林或者是画家弗里德里希,以及通过在二战的大屠杀当中感受到命运悲剧性的诗人策兰,以及和他心有灵犀的同样具有天才的奥地利女诗人巴赫曼,还有一些另外的内容也构成了基弗作品内容的矩阵,像哈巴拉神秘主义的传统,以及基弗和他的天主教自身带来的基督教的想象,再有他对共进会神秘组织,他对加密抄本这些东西的性质,以及他把纳粹历史当中很多内容给编织在一起的一种能力。应该说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基弗创造了一种自己的图像学,这个图像学带有一种压倒性的图像和一种呈现的方式,而且带有着非常强大的情感性的东西,应该说是非常淋漓尽致的、具有穿透力的。基弗在他非常大型的尤其是他的装置当中表达了他的某种洞见和愿景、愿望,在里边他把所有看画的人也牵扯到了、拽入到这种戏剧性的迷雾当中,然后让人感到触动,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到这种无助和震惊。而这种带有骚乱性的情绪又是他作品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他将整个看画者牵扯到一个历史理解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让你成为一个参与者,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你必须在要进入的意义上来解释基弗,所以基弗常常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伤口上撒盐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因为对于一个观察或者是沉浸在他的作品当中的观众、看画的人、欣赏者来说是非常痛楚的,是感到疼痛的。
主讲嘉宾:贝娅特· 海芬夏特教授
此外基弗还涉及到很多历史人物,包括神话性的人物,他经常引用像莉莉丝、三森、弗里德,还有布伦希尔德或者是布里科夫以及古希腊时代的一些女性等等,所有包括像摩根索、小屋等等所有不同引用的人物或者是内容都被他编织到一种特殊的一个语境和关联当中,里面充满着交叉的引用,应该说他编织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隐喻和象征的系统。
他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用图像来反击战争的痛苦以及存在当中所包含的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应该说基弗的画绝对不是描临,绝对不是所谓对自然的模仿,甚至也不是一种对策或者是应对,他更像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更像是一种图像性的符号,这些符号自己需言说自身,在当中自己发展出一种图像所特有的力量,并且常常也是根植于这个历史事件当中的。所以基弗总是要让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悲伤、绝望甚至是愤怒的情境当中来看过去以往的那种被忘却的真实性。 
主持人:马路教授
基弗应该说是一个大师,尤其是当我们谈论到战争、大屠杀以及人类被蹂躏的这样一个历史,如果我们要给战争屠杀和荒芜以一个面孔的话,那么基弗无疑是最佳的一个艺术家,而且他非常注意的一点是要表达人类的道德良知问题,所以他的作品当中是充满象征和符号的,尤其是他考虑的是触及到我们自身边界的问题,这种“边界”它是带有象征性的,因为他要带着观众一直来直面自己的局限性,把我们牵引到我们情感的边界、知性的边界甚至是我们羞耻感的一个边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弗要让看画的人感受到其实我们是帮凶、我们是共谋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存在的历史的和政治的不公都是因为我们的漠视和沉默而共谋的。那么基弗所有的加诸于自身的历史性的异物也表达了他对个人的一个理解,以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可能是一个有关于世界关联或者说世界意义的这样一个理解,因为他总是对于生存或者是存在以一种不断地咀嚼和反刍的方式,而结果应该是味同嚼蜡的,也就是说,基弗在这样的反刍中没有咀嚼出任何让我们觉得畏诫的东西来。相反,世界对于基弗来说在“二战”的时候便已经没落了,这个没落我们也知道基弗本身是在二战后或者说在二战后期所诞生的,其中他也在他的作品当中表达了一种信息,似乎是人们在刚一开始就把自己陷入了一个通往深渊和通往没路的途径当中去,似乎我们是无法摆脱的,因为我们的意见、所谓见识、行为已经从一开头就把我们都牵扯到这个当中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基弗认为正是人类的傲慢和狂妄自大使得我们将带着世界一同毁灭,基弗不断去阐释或者是运用的一些历史形象或者是神话人物,传说等等,恰好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也就使得基弗的画在作品当中总是表达了某种漠视论的潜质或者是歧视论的气质,他使人们纠结在一种罪责当中,因为我们所作所为的因果链条已经包含了人类的没落。
讲座现场
陌生化
作为看画的人会感到被基弗画中所包含的内涵和语境深深冲击,因为他的画不断地要求人们有新的知识、新的认识,应该说是触及到我们认知的边界,而且我们在他的大幅绘画中感到了他对我们观看的甚至是一种控制性的、一种左右的力量。因为基弗几乎是质疑一切的,他将一切我们熟识的东西陌生化。此外他面对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我们的态度会发生转变,在整个艺术鉴赏当中,历史事件本身也跟着转变。基弗对德国历史纳粹题材当中令人担忧的反人类历史非常聪慧的将姿态、行为、风景、建筑等等都给联系在一起,在随后的一些年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又赋予了场所以象征,一些新的内涵,而且这种内涵是发生着漂移和丰富的,而由他自身所创造的图像学和象征系统也是他具有的一个意义,也不断地积累下来、沉淀下来。从而使得他的这种非常具有个性化的图像系统具有了历史的一个维度,因为它包含着一种多重的叙述层面和结构,而它们互相是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他之后引用一些新的材料、自然材料,比如说用一些混凝土、铅、酸等等将这些运用在他的大型装置当中,这个都带有着他的一个特殊的非常个性化的图像学或者是图像集合的笔法和他的特殊性。因而当我们看基弗的作品并且回顾古典的图像传统的话,就会发现我们需要不断地拥有对作品的某种特定的阐读方式,也就是基弗所重新创造出来的对象或者是一种象征意义,他必须要经由看画的人重新解码,有的时候又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因为基弗他总是把看画的人引向歧途,有的时候他甚至会给看画的人准备好几块绊脚石,使得我们在阐读和解码他的作品当中步履维艰。
基弗的很多作品当中似乎提出了很多当下看来是不太受欢迎的一些题目,比如说“关于人类的罪恶感”的问题,人类的行为当中所包含的“恶”的问题,在基弗看来恰好也是人类所现有的生活道路当中所包含的极为不同的可能性。人可以在当下的一个抉择当中脱离我们所以为的冗长的平庸之“恶”的这条道路,而使得自己的命运出现新的转机。当然更多还是个体的力量非常式微的,因为我们纠缠在从一开始就在人类的摇篮当中所种下的某种罪的东西。基弗总是不断地重新来以各种方式阐释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是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在空间当中以一种比较大幅、大规模的方式提出带有道德张力的问题。
此外我们在基弗的风景画当中常常也能够看到他并不是给出一个全部,他是给出一个更为广博、更为宏大的东西当中一些片段,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可见的碎片,然而更大、更遥远的东西被肢解了,我们恰好是要从这些残缺当中去想象、去意想、去推演那个更为宏大、更为广博的东西,这也是基弗关于风景概念当中直接受德国浪漫主义所开启的一个东西,同时也是他的图像学当中一个作为集体记忆的一个普遍的图像资源或者是宝藏。通过这种方式基弗就能够有能力让人们不断地回溯他所熟悉的东西,并且在这个熟悉基础之上运用自己的图像学在图像当中阔步开去,向未知的领域挺进,所以他的“风景”当中,还有他本身非常大规模的色彩本身就具有大幅的肌理,就使得他自身构成了某种身体性的东西,尤其是他在80年代以后用很多材料,像稻草等等的作《海德马尔基荒原Haar Margarethe》,这个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让我们想到了保罗策兰的诗歌《马格里特的金色的头发》他用艺术的方式包涵象征来呈现、再现了这个诗的意象。
讲座现场
图像的力量有的时候还体现在他在主题上的简洁和清晰,因为基弗有这样一种能力,他似乎非常明确地指示着人们的观看,有的时候是让我们俯视的,有的时候让我们仰视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呈现了风景的无限和深度,并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深度和无限。
基弗的绘画同样能够彰显一种力量,我们在当中能够再次发现他的由来在哪儿,也就是说他所具有的知识的视域是怎样的,尽管我们一再提到这种已经陈旧的知识的视域能够通过基弗的作品再次被激活。从1969年开始,基弗的语言也将很多文字化入他的画作当中作为图像的内容,他自己并不做任何区分。在他看来整个绘画甚至整个文学所有的一切都是处于关联之中的,因为他所关乎的无非是我们如何来应对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如何来应对所谓巨大的深深的黑洞,如何来应对好像似乎是我们无法进入的这样一个中心。很有意思的是,这里面文字和语言对于他来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他所用的图像书或者是图片书当中重要的内容,因为他经常用铅、色彩等构成非常复杂的图像作品,而且都是柔在一起的。此外不仅仅是文字,像书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基弗非常喜好的一个主题,似乎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一个魔力,从古老的图书馆当中发起,比如说他会提到以弗所的图书馆,当时以弗所曾经被看成甚至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因为当时汇集了人类非常重要的图书馆和知识,是人类有意识的要把知识以文字的形式传递下去,以此来应对或者是抵抗毁灭、破坏和遗忘所带来的厄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应对梭格的所谓从容不迫和不动心的淡忘。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样一个图书馆它恰好是人类汇集知识的一种方式,此外基弗非常关心的是人类如何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应对人类所遭遇的历史和在历史当中所展开的命运,其中包括比如说像人类在纳粹统治下所有的历史、屠杀的历史以及人自己对这段历史整个的加工问题。在处理这段历史当中基弗不仅采用了犹太教的传统,同时也将犹太教传统和他本身所在的基督教的传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基弗总是不断地促进他的绘画的观看者重新发现,重新寻找,从一个自身所有的冗长的语境当中突破出来,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寻找一个新的可能性。在80年代以后他还曾经做过一个作品大概是说我要与所有的印度人握手。他还曾经呈现过1460年-1523年达伽马著名的航海家达伽马,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借用。基弗表达了人与不自然的关系,在一种环绕的循环当中好像杳无一物的东西。此外基弗还呈现他自身,我们能够看到他自身在一个风景当中裸露的,既是呈现他非常脆弱的一个东西。总之,基弗应该说以他的这种裸露的,但又是一种直立的,一种非常直面冲突的对应的方式,让他的观察者不仅仅是面对自然,也不仅仅是面对一个似乎不可视,但是能够呈现的那样一个有无限威力的神力的一个东西,是人把自身放置在中心,慢慢的好像无限的、无垠的风景都撤回到背景,而仅仅呈现着看画者所面对的一个自我。首先重要的还是一个追问的人,好像这个追问的人能够在这个所谓另外一个自我当中来探究自我,探究他全部的同一性的问题、身份的问题。这个既是一个他肉身在场的东西,同时也是一个精神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好像基弗以这种非常猛烈的方式,似乎一直让每一个个体来向世界和向他的存在进行永远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