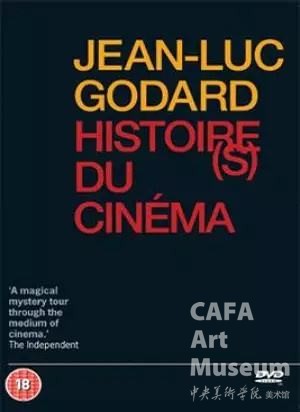
我使用“感知共同体”(community of sense)一词并不是指集体性,后者是由某些共同的感知形成的。我理解它是一种可见度与可理解性,把不同事物或实践置于相同的意义之下,因此形成某种共同体感知。感知的共同体是时空的某种切割,融合了实践、可见性形式以及可理解性模式。我将这种切割与联系称作可感知物的区分。
含有大量技巧的产品,如绘画、表演、舞蹈、演奏音乐等等,以可见性的特定形式来掌握,它们将前述诸项置于共同性中,并以其联系性来形成特定的共同体感知时,才有艺术。人类已经认识雕塑家、舞蹈家或音乐家几千年了。人类仅仅把艺术当作是单数、大写的形式来了解认识才两个世纪而已。人类已经知道艺术是某种空间的分隔。开始时,大写的艺术不是由绘画、诗歌或旋律组成的。首先,它是由空间环境构成的,例如,戏剧、纪念碑或美术馆。针对当代艺术的讨论并不是关于作品的比较价值高低的讨论。它们都是关于空间化这回事儿的:例如让视频显示器立在雕塑前面,或各种藏品散落在地板上,而不是把绘画挂在墙上。它们都是关于由图画框架所传递的在场的感知与取代它的屏幕所传达的缺席的感知。这种讨论涉及东西分配到墙上或地面上,或放进框架里或播映在屏幕上。它涉及一个空间环境与另一个空间环境之间或在场与缺席之间的转换中所发生的共同物的感知。
一种物质的分隔总是同时也是一种符号的分隔。剧场或美术馆塑造了有些可以给予的东西与某些不可给予的东西之间的共同存在与兼容的感知。他们塑造了可见物与可理解物之间,或在场与缺席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也包括嵌在它们的空间里的共同体感知与其他的经验领域所框定的其他共同体感知之间的共同体形式。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同的感知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这是说,艺术和政治并不是两个永久的现实,关于这两个现实,我们不得不讨论它们是否必须相互关联。事实上,艺术与政治是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共同物的偶然性构成。正如并不是总有艺术的(尽管总是有音乐、雕塑、舞蹈等等),也并不是总有政治的(尽管总是有权力与满意的形式)。政治存在于特定的感知共同体里。它的存在就是对其他的人类集会形式的异见式的补充,是作为客体与主体、地方与身份、空间与时间、可见性与意义的有争辩性的重新分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学行为”,其含义是指,它与国家权力被集合进集体的艺术品中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被本雅明命名为“政治的美学化”。
所以,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可感知物的两个分隔部分的关系。它假定,这两个术语本身都是一样的。艺术为了能够按照本身来存在,它必须等同于一个特定的、将实践、可见性形式和可理解性模式统一起来的认同体制。艺术为我们而存在的认同体制需要有一个名称。两个世纪以来,它被称作“美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的美学与美学的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美学的政治的含义呢?这个问题主要依赖前一个问题:我们对于名为“美学”的东西是怎样理解的,这个术语定义了什么样的感知共同体。
关于这个题目,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宏大叙事。根据这个宏大叙事,它就是著名的现代主义范式,“美学”是指一种自律领域的建构。它意味着,艺术品孤立在它们自己的世界里,它们异在于其他的经验领域。在这个世界里,它们受到内在的合法性原则评价:通过形式、美或媒介真实的标准。由此,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关于艺术的政治性的结论。第一,艺术品塑造了一个纯粹美的世界,它没有任何的政治的含义。第二,它们形成一种理想的共同体,让人们怀有旨在超越政治冲突的感知共同体的绮丽幻想。第三,它们在自己的领域里获得相同的自主,这种自主是现代艺术的核心,也在民主政治或革命政治中被追求。
根据这个叙事,艺术、自律与现代性之间的认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垮掉了。它之所以垮掉,是因为社会生活与商品文化的新形式伴随着新的生产、复制、通信技术,就使得无法保持艺术生产与技术复制、自律的艺术品与商品文化的形式、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之间的边界。边界被如此模糊应该等同于“美学的终结”。这种终结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激烈争论。例如在哈尔·福斯特主编的一本书里有过整理,这本书叫《反美学》。收集在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文章是道格拉斯·克里木普(Douglas Crimp)写的《论博物馆的废墟》。已成废墟的“博物馆”就是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克里木普的论述主要是依据马尔罗的博物馆中对摄影的双重使用的分析。一方面,只有通过摄影的复制,才有可能出现“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摄影自身使得石雕印在其中的页码紧挨着一件上了颜色的圆形浮雕或浮雕旁,或使得马尔罗去比较安特卫普的鲁本斯的细节与罗马的米开朗基罗的细节。它可以让作者用“艺术的精神”的在场来代替作品的经验性。不幸的是,克里木普指出,马尔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他承认摄影不再是艺术品的复制品,而它们自身就是艺术品。为此,他迫使构成博物馆的同质化的同质化手段依赖于它的异质化。异质化在博物馆的核心区被重新确立起来。所以,博物馆隐藏的秘密就可以公开地展示出来。这就是罗伯特·劳申伯格几年后要做的事情,他用丝网把委拉斯贵支的《镜前的维纳斯》印在画布上,包括了很多蚊子和一辆卡车的图像,或印在直升机公司或水塔上,或印在华盛顿雕像顶上以及汽车钥匙上。通过摄影,劳申伯格把博物馆散布到每一个作品的表面上。马尔罗的梦想变成了劳申伯格的玩笑。让人有点烦恼的事实是,劳申伯格自己显然并没有理会这个玩笑,而是相反,他肯定了马尔罗过时的对人类的良知的宝库所保持的信念。
我认为,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就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这个证明到底证明了什么?如果马尔罗的梦想可以变成劳申伯格的玩笑,那么,为什么不是相反:劳申伯格的玩笑能否倒过来变成马尔罗的梦想?确实,这种颠倒几年之后将会出现:在八十年代末,著名的偶像破坏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被赞誉为是后现代实践的原型,他在拍摄他的《电影史》(是马尔罗的纸上博物馆的完全翻版,图1)的时候,他把每一件东西与任何东西混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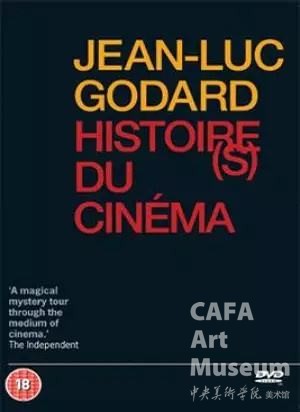
图 1 戈达尔,《电影史》(1A“所有的历史” 封面)
让我们来说明一下:“想象的博物馆”存在着矛盾,只要你首先假定博物馆等于异质化,即它是致力于艺术品的特殊性的庙堂,那么,这个矛盾就证明了后现代断裂;其次,相反地,摄影意味着异质化,即它意味着无聊的无限复制;第三,仅仅是摄影就使得我们都可以把石雕、斯基泰人的胸章、米开朗基罗放到同一个页面上,把镜前的维纳斯与一把汽车钥匙或一座水塔放到同一个画布上。如果这三个说明被证明是对的,那么,你就可以得出结论:通过摄影所实现的想象的博物馆也就意味着博物馆的坍塌,即它标志着异质化的胜利,它打碎了美学的同质化。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内容全是真实的?首先,我们怎么知道博物馆意味着同质化以及它致力于艺术品的独特性和光晕孤独感?我们怎么知道这种光晕孤独感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艺术观点中形成的?让我们追踪一下高级艺术最受庆贺的时期,大约是在1830年左右。在那个时候,黑格尔的学生出版了他的《美学讲演录》。同时,大众杂志如法国的《图画杂志》开始使用石版复制品,以期将世界艺术珍品提供给广泛的读者。也是在这个时候,巴尔扎克出版了第一部他签名的小说《驴皮记》(图2)。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拉斐尔走进奇宝店的展厅里,他看到的是:
鳄鱼、猴子和大蟒的标本向教堂的彩绘玻璃微笑,像是想咬那些半身雕像,又像是在漆器后面奔跑,或在玻璃吊灯上爬行。有一只雅科托夫人1画的拿破仑像的塞弗勒瓷瓶,放在一只献给塞索斯特里王2的狮身人面雕像的旁边。......拉图尔3用彩粉画的杜巴里夫人4像,头上有一颗金星,赤裸的玉体在云端若隐若现,她像是用淫荡的眼光来欣赏一只印度烟袋......一只抽气机竟使威严庄重的奥古斯特5大帝失去一只眼珠。好几幅大革命前的法国市长和荷兰市长的肖像摆在那里,他们屹立在这一大摊杂乱的古物中间,像他们生前那样冷酷无情,以苍白的冰冷的眼光凝视着这一切。6
这段描述看起来像是劳申伯格的混合绘画的精准预言。它形成了一个商店与博物馆、民族志博物馆与美术馆、艺术品与日常材料之间的区别空间。为了模糊所有的这些边界,并不需要后现代的断裂。如果摄影可以有助于文献获得想象的博物馆效果,那么,这是因为文献在它的各个页面上已经模糊了摄影后来对画布的模糊。当摄影与绘画结合起来就将画布变成了“印刷品”(版画)时,这种摄影的“文献历史”就跃然出现了。

图2 巴尔扎克,《驴皮记》(译林出版社,郑永慧译,1998年)

图 3 罗兰 • 巴特,《明室》(文化艺术出版社,赵克非译, 2003 年)
这是第二点:我们是如何知道摄影等于异质性、无限可复制性以及光晕的丧失?克里木普发表他的文章的同一年,也有一篇论摄影的重要文章发表:罗兰·巴特的《明室》(图3)。在这篇文章中,巴特公开地推翻了主流的摄影观点。他认为摄影是特殊性的证据。在随后的几年里,在摄影已经被当作是最适合后现代拼贴的人工品之后,就被看作是一种圣维罗妮卡的符号,是纯粹与特殊在场的标志。
这意味着这个观点可以被推翻。博物馆意味着同时的同质化与异质化。摄影意味着复制性和特殊性。摄影的复制性凭借自身能力不能形成新的感知共同体。它不得不在更广泛的可见性形式与可理解性的情节范围内被掌握。它不得不尽各种可能去增强或降低在场形式或意义的过程。劳申伯格使用摄影并没有打开新的时代。它只是额外地补充了反对现代主义将“平面性”等同于自律艺术和绘画的独立的证据。它加强了斯特劳·马拉美的“纯粹诗”的读者已经知道的东西:平面性不意味着媒介的特殊性;它意味着交换的表面;诗歌的时间与线条在空间的描绘之间的交换;行为与形式之间;文本与绘画或舞蹈之间;纯粹艺术与装饰艺术之间;艺术品与属于个体或集体生活的物品或表演。
如果生产出反对格林伯格的平面性范式的新证据,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的话,那么,显然还另有原因。这是因为有一个确切的美学政治在那个“形式的”范式里运作着:人们用政治自由和平等的承诺给这个政治信托了自律作品,用另外的美学政治妥协了这个政治。这个美学政治是让艺术在创造新的集体生活中压抑自身的美学政治。
这里的要点是,“艺术自律”的极端性是将美学自律与某些政治或有点形而上的共同体实施联系起来的更大的图谋的一部分。美学——我的意思是艺术确认的美学制度——使其自身的政治成为必要。但是,政治将自身分为两个竞争的可能性,两个美学政治,也就是意味着两个感知共同体。
众所周知,美学诞生于法国革命时期,它从一开始就与平等紧密相连。但问题是,它与两个竞争的平等形式相连。一方面,美学意味着约束和等级体制的坍塌,这个体制构成了艺术的再现制度。它意味着主题、类型、表现形式的等级被打散了,是这些东西将值得或不值得进入艺术领域的物品分隔开,或将高级类型与低级类型分隔开。它意味着艺术场域的无限开放,它最终又意味着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创作与无名生活的边界的消除。艺术的美学体制并不是伴随着颂扬特别天才(他们生产了特别的艺术品)而开始的——这是很多理论家仍然如此认为的。相反,它始于18世纪的一种确认:即原型的诗人荷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的诗歌不是艺术品,不是任何艺术典范的极致,是一件汇总的故事的百衲衣,它表达了尚处于婴儿时期的人类的情感与思考方式。
所以,一方面,美学意味着这种平等,是与法国国王被砍头和人民获得主权一起来的。现在,这种平等最终意味着艺术和生活的不可分辨。另一方面,美学意味着艺术品是在经验的特定范围内被掌握——用康德的话说——在这个范围里,它们摆脱了与知识对象或与欲望对象的感官联系的形式。它们仅仅是对应着自由的游戏的“自由的表象”,意指知性与感官之间的非等级关系。席勒在其《人类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描述了去等级化的政治后果。“审美状态”定义了感官平等的范围,其中,积极的理解力高于被动的感知这种说法不再合法。这意味着它打散了感知的分隔,这种分隔在传统上是通过分开两种人文学科来赋予它主导地位具有合法性。上流阶级的权力据认为是主动性驾驭被动性的权力、理解力驾驭感性的权力、有修养的感知驾驭粗糙的感知的权力,等等。审美经验为了放弃这种权力,建构了一种平等,这将是与主导地位相反的东西。席勒反对法国革命中所实施的那种针对政治革命而进行的感知革命。政治革命完全失败了,因为革命权力扮演了传统的理解力角色——即国家,将法律强加给感知的事务——即群众。唯一真实的革命将是推翻驾驭被动感知的积极理解力的权力的革命,推翻知识与行动阶级统治被动与欠发达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因此,美学意味着平等,因为它意味着禁止艺术被划出边界。它指平等,因为它意味着艺术被建构为人类经验的一种单另的形式。这两个平等是对立的,但是它们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希腊女神像允诺了解放的未来,因为女神“空闲”、“矜持”。她允诺这个,是由于她与我们的知识和欲望是分离的,是走不进的。但是与此同时,雕像又允诺了这个,因为它的“自由”——或“心不在焉”——体现了另外的自由或不在乎,这是创造了它的希腊人的自由的观点7。现在,这个自由意味着第一个自由的对立面。这就是生活的自由,根据席勒的观点,它不会把自己分裂成单另的、有差别的存在形式。对他而言,艺术是和宗教一样的,宗教是和政治一样,政治是和伦理一样:一种综合在一起的方式。结果是,艺术品的单另性允诺对立面:一种不知道艺术就是经验的单另的实践与场域的生活。美学政治就依赖于这种原初的矛盾。这种两个对立的平等的矛盾联系可以走向(历史上也确实走向了)政治的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旨在连接两个平等。这样,“感知共同体”意味着在审美经验中体验到的平等与自由不得不转向共同体的存在形式:集体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将不再是形式与表象的问题,但将是体现在态度中的问题,体现在日常感官经验的物质性的问题。共同体的“共同”因此被编织进有生命的世界的结构中。这就意味着审美平等与自由的单另性必须通过它的自身压制来获得。它必须用共同生活的单另形式获得,其中,艺术与政治、作品与休闲、公共与私人生活都是一样的。审美革命的计划也是如此,它在真实的生活中获得政治异见,审美快乐只能在表象中获得。这个计划第一次是在两个世纪前的“日耳曼唯心论的最古老体系计划”中提了出来,提出用人的有活力的身体(由哲学激活为神话)来代替已死掉的国家权力机制。它不断地得到复兴,既在作为“人类革命”(意指政治的自我压制)的革命计划中、又在作为单另的实践的艺术压制自身(将自身等同于生活的新形式的阐释)中。它激活了19世纪英国的奇异的工艺之梦,也激活了20世纪德国的工业同盟或包豪斯的技术成就,还有诗歌的马拉美之梦——“为未来做准备”,以及苏联的至上主义、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艺术家的具体参与。它激活了情景主义建筑的计划,也激活了德波的漂移(dérive)或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图4)。我认为它活在哈特与内格里的诸众(multitude)的弗朗切斯科共产主义的当代版本中。这是通过全球网络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来实施的,它爆破了帝国的边界。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政治与艺术必须获得它们的自我压制,以利于不再分离的生活的新形式。

图 4 博伊斯带领学生清扫
相反的,第二形式断开了两个平等的联系。它将审美经验的自由与平等空间从艺术与生活的无限等值域给断开了。它将感知共同体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感知共同体之间的不可还原的对立,这两个就是联系与断开的共同体。一方面,存在活着的经验的诸多共同体,意味着异化的生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依赖于感知与意义的初始的分离。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叙事中,这就是尤利西斯的理性与海妖的歌声以及航行的分离。8异化的生活的共同体是在它的对立面的欺骗表象中获得的。它在审美生活与商品文化的同质性表象中获得。与这个假平等、假感知共同体相对的,是由审美经验自律形成的共同体,也由它对所有的其他的经验形式的异质化形成。标准的现代主义范式仅仅是那个共同体的一部分和表面的解释,忘记了它的政治内容。艺术的政治行为就是拯救异质的感知物,这是艺术的自律及其解放力量的核心。在那个美学的政治中起作用的感知共同体就是基于感知与意义相连与分离的共同体。它的分离性“有意义”的程度,就是它不是纯粹形式的避难所。相反,它表现出分离性与不可分离性的关系。作品的自律完美必须揭示出它自身的矛盾,使得异化的痕迹出现在调和的表象中。它要把尤利西斯的理性与海妖的歌声调和起来,而它同时又使它们不可调和。
在这个政治中,重要的不是多么强地保持了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或流行艺术之间的边界,就像它保持了“感知”的两个世界的异质性那样。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后现代主义辩论家认为当劳申伯格把委拉斯贵支的复制品和一把汽车钥匙都放在画布上的时候,现代主义的“政治性”范式就崩溃了,那么他们则打中靶子。只有分开感知的两个世界的边界崩溃了,才会威胁到这个范式。阿多诺有一次坚决声称我们不再可能听到——不再承受——19世纪沙龙音乐的某些弦乐,他说,除非每一件事都是诡计。轮到利奥塔,他会说你不能把具象母题与抽象母题都混合到一张画布上;感知到并欣赏这种混合的趣味不是趣味。众所周知,有时候,看起来那些弦乐仍然可以听到,你仍然可以看到具象与抽象母题混合到同一张画布上,甚至仅仅从日常生活里借用些人工品并展示出它们就制造了艺术。但是,这标志着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并不是极端的。该范式没有被这种启示打碎,它被导入快速的飞行中,它不得不重申感官经验的激进异质性,其代价是不仅阻止了任何的政治的感知共同体,而且压制了艺术自律自身,将之转换为纯粹的伦理证据。这种转向在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美学思想中最明显了。罗兰·巴特反对去世的母亲的照片的特殊性,不仅仅是反对语义学家的阐释活动,也反对摄影自身的艺术借口。戈达尔强调图像的象征力量或句子的节奏,其代价是不仅破坏了旧的叙事,也破坏了艺术品自身的自律。在利奥塔那里,笔触或木材变成了心灵被他者的力量奴役的纯粹证据。他者的第一个名字是aistheton(感知界),第二个是法律。最终,政治和美学消失在伦理学中。艺术的政治性的现代主义范式的这种逆转是与思想的整体趋势同步的,这种趋势消融了例外与恐怖的原型政治(archipolitics)中的歧感性(dissensuality)。在此,只有海德格尔的上帝能拯救我们。
我很快地勾勒了这两种感知(意义)共同体,为的是提醒我们下面的情况:政治化艺术的计划——例如用批评式艺术的形式——总是被政治性的形式所预示,政治性的形式又是必然地出现在可见性与可理解性的形式中,这就使得艺术可以被这样确认。我们是在平等的两种形式的相互作用中确认艺术,它附属于它的分离性,也附属于它的非分离性上。我们通过它的自律和它的异质性的辩证法来确认它。那么,做政治的或批评的艺术或采取政治的艺术观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平等的两个审美形式之间的关系的特殊协商中来定位它的权力。事实上,批评的艺术是一种介入两个美学政治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这种协商必须保持某种使得审美经验趋向集体生活的重构的紧张,也保持某种将审美感受(sensoriality)的力量从其他的经验领域撤出来的紧张。它必须从艺术与生活的区别地带借用激起政治理解性的联系。而且它必须从艺术品的分离性那里,借用增强了政治能量的感知的陌生性的感知(sense或意义)。政治的艺术必须是某种这些对立面的拼贴。拼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批评的艺术、“第三政治”的重要过程,它必须在美学的两个政治之间编织它的通路。拼贴在混合委拉斯贵支与汽车钥匙之前,就将美学的几个另类政治做了混合,并提供了与理解性的不定的形式进行协商的产品,促进政治性的不定的形式。它框定了小的感知共同体,小的借用自异质的领域的元素共同体。它从不同的经验领域那里吸取元素,从不同的艺术或技术那里获取拼贴形式来建立起特殊的异质性形式。如果布莱希特在20世纪为政治艺术保持了一种原型,那么,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他持久的共产主义信念,相反,是由于他协商这些对立面的关系的方式,将政治教条的学术形式与音乐或卡巴莱歌舞表演的喜悦混合起来,或是用散文讨论纳粹权力对菜花的寓言。政治或批评艺术的主要过程包括开始相遇异质性元素,可能还有它的冲突。这些异质性元素的冲突假定可以引起我们的知觉的断裂,可以暴露隐藏在日常现实背后的事物的某些秘密的联系。这种隐藏的现实可能就是梦境与欲望的绝对权力,被资产阶级生活的散文遮蔽着,因为它就在超现实主义的诗学中。
这样,政治艺术意味着创造这些辨证冲突或异见的形式,它们聚合在一起的不仅是异质性元素,而且是两个政治感知性(sensoriality)。异质性元素被聚合在一起,是为了造成冲突。现在,冲突同时是两个事物。一方面,这是启蒙的一道闪电。异质性元素的相互关联显示出它可以被识别。它指向权力与暴力的某些秘密。布莱希特的《教父亚涂发迹史》戏剧将蔬菜和高级修辞联系起来,它传递了政治信息。但是另一方面,只要诸多元素的异质性抵抗着意义的同质性,那么冲突就产生了。蔬菜还是蔬菜,与高级修辞并置在一起,它们没有任何的信息,它们应该用它们的模糊性来增强政治能量。最终,不规则元素的简单并置被赋予了政治权力。在戈达尔的电影《美国制造》(图5)中,主人公说:“我的印象是置身在迪士尼乐园的电影中,由亨弗莱·鲍嘉(HumphreyBogart)扮演,所以是置身在政治电影中。”这样,不规则元素的简单关系出现了,因为辨证冲突见证了冲突的政治现实。

图 5 戈达尔,《美国制造》
政治艺术是一种协商,不是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协商,而是在两个美学政治之间。只有连续地游走在边界上以及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的缺席中,第三条道路才有可能。寓言以及寓言的揭露的布莱希特式身份假定你可以游戏在艺术与菜花、政治与菜花之间的关联以及无关处。这样的游戏假定蔬菜自身具有双重存在:一个存在是其中的蔬菜与艺术和政治没有关系,另一个存在是其中它们与两者有强烈的关系。政治、艺术和蔬菜的关系存在于布莱希特之前,不仅存在于印象派静物画中,它们复兴了荷兰传统,而且也存在于文学中。左拉写的一部小说《巴黎之腹》,特别使用它们作为政治与艺术符号。小说根据极端不同的两个主人公写成。一方面,有一个年老、贫穷的革命家从穷困中来到巴黎的磊阿勒区,他被那里的潮水般的白菜震撼了——意思是潮水般的消费。另一方面,也有印象派画家歌唱白菜史诗、现代性史诗、磊阿勒区的玻璃钢铁建筑以及堆积如山的白菜,它们将现代美都做了寓言化,与老式的、以附件的哥特式教堂为象征的悲催的美形成强烈对比。白菜的政治寓言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艺术、政治与蔬菜的关联——艺术、政治与消费的关联——已经作为一套移动的边界存在了,使得艺术家可以跨越边界,让异质性元素的关联有意义,游戏着它们的异质性感官能力。
这就意味着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的混合,或艺术与商品的混合,都不是60年代的发现,它们已经实现了并破坏了现代艺术及其政治潜力。相反,由于这种混合、由于连续的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商品的边界跨越过程,政治艺术已经成为可能。这个过程深深地介入到艺术的美学体制的历史中。你无法让高级艺术的庆典时代去反对高级艺术的平凡化或模仿时代。艺术在19世纪初一被建构为存在的特定领域,它的产品就开始沉落为平凡的复制、商业和商品。但是一旦它们这样做了,商品自身也就开始按相反方向运动——进入到艺术的领域。它们的权力就直接被等同于现代生活的强大权力与美,如左拉的白菜史诗所描绘的。它们也可以因为过时、无法进行消费而被置于艺术的领域,因此,转变成审美(非功利的)愉悦或神秘的兴奋的对象。超现实主义诗学以及本雅明的寓言理论或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都是在这种边界跨越中繁荣起来的。所有在艺术与商业的模糊关系(直至许多当代装置)中起作用的批评艺术形式也都是这样繁荣的。他们将借自艺术传统、政治修辞、商品文化、商业广告等等的异质性材料都统统混合起来,为的是揭露高级艺术或政治与资本主义统治的关联。但是它们可以这样做,是由于持续进行的、已经消除了这些边界的过程。批评艺术在这种连续的边界跨越中得以繁荣,这是双向的诗学散文化与散文诗学化的过程。
如果这个有意义,那么,就有可能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来重新(希望这样)确定诸多政治问题,这是在讨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当中都涉及的。在当代艺术中存在风险的不是现代主义范式的命运。它的合法性既不比过去更弱,也不更强。在我看来,它总是一种对艺术的美学体制的辩证法进行的限定性阐释。存在危险的是第三美学政治的命运。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仍然是现代、已经后现代或甚至是后后现代,问题是辨证的冲突究竟发生了什么、批评艺术的公式发生了什么。我将提出几个例子,试做可能的解答,也提到过去几年的若干展览,作为对60年代或70年代的艺术的比较要点,因此,也提出若干重要的转向标志。
第一个例子。三年前,巴黎国立摄影中心举办了一个展览,叫“背景噪音”(BruitdeFond)。展览将最近的作品和七十年代的作品并置在一起。在后者当中,你可以看到马萨·罗斯勒(Martha Rosler)的系列作品《将战争带回家》(图6)。这是摄影拼贴,把美国家庭幸福的广告图片和越南战争的图片拼贴到一起。就在这个作品旁边,是另一个与美国政治有关的作品,采取了相同的两个元素的冲突的形式。这个作品叫《世界的时间》,作者是王度。作品由两个部分组成:在左边,是克林顿夫妇,用波普方式表现的,是一对蜡像馆式的人像;在右边,是巨大的库尔贝的《世界的缘起》的雕塑,众所周知,这件作品表现了女人的性器官。这样,在两件作品中,美国幸福的图片都被并置了一个隐藏的秘密:在马萨·罗斯勒的作品中是战争与经济暴力,在王度的作品中是性和亵渎。但是在王度的作品中,政治冲突性和陌生感都消失了。留下的是去合法化的自动效果:性亵渎消除了政治合法化,蜡像消除了高级艺术的合法化。但是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消除合法化。机制在围绕自身旋转。事实上,它起到了双重的作用:去合法化效果的自动性和围绕自身旋转的意识。

图 6 马萨 • 罗斯勒,《将战争带回家》(系列作品之一)
第二个例子。三年前在巴黎有另一个展览,叫作“看:头脑中的世界”。它提出用不同的装置来记录一个世纪,其中有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的装置《电话预订》(Les abonnes du telephone,图7)。这个装置的原则很简单:展厅的两侧有两个柜子,里面有世界各地的电话簿,中间有两张桌子,你可以坐下,翻阅你喜欢的电话簿。这个装置提醒我们另一件九十年代的政治作品,克里斯·波顿(Chris Burden)的《另一个越南纪念碑》。当然,《另一个越南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匿名的越南受害者的纪念碑。波顿随意地从电话薄上挑出越南人的名字,把它们写在纪念碑上。波尔坦斯基的装置仍然涉及的是匿名的问题。但是匿名没有深入地嵌入富有争议的情节中。它不再是给证人没有留下名字的那些人给予名字的问题。匿名的名字正如波尔坦斯基所言,变成了“人性的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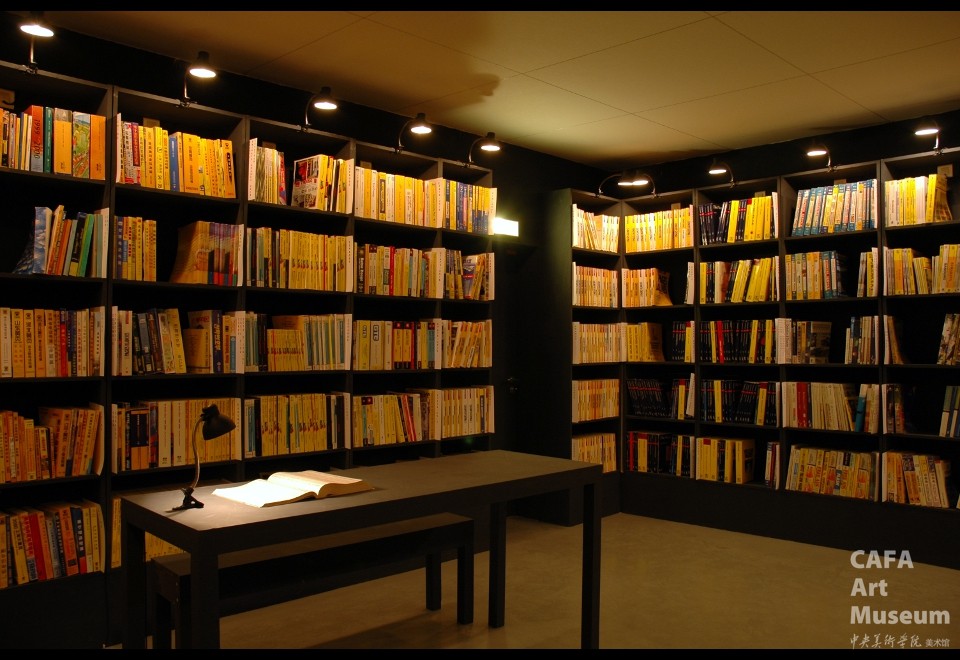
图 7 克里斯蒂安 • 波尔坦斯基,《电话预订》
第三个例子。在2003年,纽约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名为“移动的图片”(Moving Pictures)。目的是说明当代艺术中广泛使用的可复制媒介是如何深深扎根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批评艺术实践中,既质疑了主流的社会老套成见或性的成见,也质疑了艺术自律。然而,在旋转厅里展出的作品说明了摆脱直线的重要转向。例如,比克罗夫特(Vanessa Beecroft)的录像作品展示了裸体的女子站在美术馆的环境中,这个作品仍然被看作是对艺术中的女性成见的批判。但是,显然这些沉默的裸体遵循了另一条方向,逃离了任何的意指或意指的冲突,比任何类型的女性主义批判都更能唤起藉里柯(Giorgiode Chirico)的形而上绘画。当你沿着古根海姆的圆形坡道向上走时,许多录像、摄影、装置和录像装置增强了一种新的陌生感,一种日常生活的平凡表现带来的神秘感,而不是对它们的批判。在莱涅克·迪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的模糊不清的少年照片中(图8),也在格雷戈里·克鲁德森(Gregory Crewdson)的电影一样的日常事件的陌生感再现中,或在波尔坦斯基的装置(由照片、电气设备和灯泡组成,根据作品,它们象征了大屠杀的死者,或者象征了少年时光的转瞬即逝)中,你都会感知到这些。在展览的上部,是从冲突的辩证艺术退回到神秘的象征主义艺术。最后是比尔·维奥拉(BillViola)的视频装置《白天出行》(Going Forth by Day,图9),由一组循环的壁画组成,包含了出生、生命、死亡与复活的循环,也包含了火、气、土、水的循环。

图 8 莱涅克 • 迪克斯特拉,《科沃布热格,波兰, 1992 年7月12日》

图 9 比尔 • 维奥拉,《白天出行》
我们用这三个例子(是从许多其他可能的例子中选出的)可以勾画出今天的美学的政治的问题答案:批评艺术的异见形式发生了什么?我会说美学异见的辩证形式已经分裂成四个主要形式。第一个形式是:玩笑。在玩笑中,异质性元素的联合仍然被视为紧张或对立,指向某个秘密,但是不再有秘密。辩证紧张作为游戏又被带回来,是在揭露了权力秘密的过程与去合法化的普通过程(成为统治的新形式:去合法化的过程由权力自身、由媒介、商业娱乐或广告产生)之间的不可识别性上玩这个游戏。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王度的作品的情况。今天许多的展览都是在玩这个相同的不确定性。例如,有一个展览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时候,标题是“让我们娱乐吧”,等巡展到巴黎时,改为情景主义标题“超越景观”。这个展览玩了三个层次:高级艺术的波普艺术嘲笑、资本主义娱乐的批评谴责和作为景观的对立面的德波式游戏观。
第二个形式是:收集。在收集中,异质性元素仍然被混在一起,但是它们不再聚合起来去激起批评冲突,甚至也不再玩批评权力的不确定性。它们积极地去努力收集普通世界和普通历史的遗迹和证据。收集也是再收集。所有物件的平等——艺术品、私人照片、用品、广告、商业录像——因此都是成为共同体的生活的档案痕迹的平等。我提到维奥拉的展览——“头脑中的世界”,它试图去重新收集一个世纪。当你离开波尔坦斯基的展厅,例如,你可以看到汉斯-彼得·费尔德曼(Hans-Peter Feldmann)创作的一百张照片,再现了某人从一岁到一百岁的每一年龄(图10),还有其他许多的装置记录了普通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潮流的许多其他例子。显然,它与下面这句今天不断听到的话是一致的: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世界”,“社会契约”被打破,艺术家必须参与到修复社会契约或社会网络的斗争,将所有见证共同的人性的痕迹都呈上前台。

图 10 汉斯 - 彼得 • 费尔德曼的展览“100 Years”在 MoMA PS1展出现场
第三个形式是:邀请。我提到《电话预订》是如何邀请参观者取一本架子上的电话簿,然后随意打开它。在同一个展览的某个地方,他们受邀从一堆东西里取出一本书,坐在地毯上,表示某类儿童的童话岛。在其他的展览上,参观者受邀喝汤,彼此接触,参与到新的关系形式中。这样的活动之前都在尼古拉·布瑞奥的关系美学概念中得到系统化阐释:艺术不再创作作品或物品,而是创造短暂的环境,促进了新的关系形式。如他所说,艺术家通过若干微小的服务,就为弥合社会契约的隔阂的事业做出了贡献。9
第四个形式是:神秘。神秘并不是谜,也不是神秘感。自从马拉美的时代以来,它意味着一种将异质性元素糅合在一起的特别方式。例如,就马拉美而言,是诗人的思想、舞蹈家的脚步、扇子的展开或一支香烟的烟霭。神秘反对那种强调诸多元素的异质性的辩证冲突(为的是展示一个由对抗构成的现实),它提出一种类比——一种陌生的熟悉感,见证着普通世界——其中,异质性现实是用相同的织物编织成的,彼此总是可以用隐喻的兄弟会来相互联系。
“神秘”和“隐喻的兄弟会”是戈达尔在他的《电影史》中使用的两个词语。这部作品是一个恰当的有趣案例,因为戈达尔使用了异质性元素的拼贴,就像他总是那样使用的,但是他使它们产生出和它们20年前的含义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戈达尔在《电影史》里有一段精彩的段落,他融合了三个图像:首先是乔治·史蒂文斯的电影《郎心如铁》的剧照,展示了伊丽莎白·泰勒扮演的相爱的人的幸福,沐浴在太阳之下,她的身边就是她爱着的蒙特戈梅·里克利夫特;第二个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ück)的死者的图片,这部电影也是史蒂文斯几年前拍摄的;第三个是一幅抹大拉的玛丽亚图像,源自乔托画在帕多瓦的壁画。如果它是20年前制作的,这个拼贴只会被理解成是辩证冲突,它谴责了隐藏在高级艺术和美国幸福背后的秘密。但是在《电影史》中,谴责的图像被变成拯救的图像。纳粹种族灭绝、美国幸福和乔托的“非历史”艺术的图像都见证了图像的证据力量,它们赋予生者与死者在“世界的地位。”辨证冲突变成了一种同在(copresence)的神秘。神秘是象征主义的核心概念。象征主义的回归显然已在议程之中。当我使用这个术语时,我不是指象征主义神话学的复活的景观形式,也不指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的梦想,如马修·巴尼的作品那样。我也不是仅仅指象征主义的有效使用,如我前面提到的维奥拉的作品。我指的是更加谦虚、几乎不可察觉的方式,在我们的美术馆、画廊里所汇集的物品、图像和标识的藏品正用这种方式越来越从异见的逻辑转向神秘的逻辑,转向同在的证据。
从辩证法转向象征主义显然与当代转向有联系,方式就是我称之为的政治美学,指的是政治框定了一种普通舞台的方式。这种转向有个名字,它就是“异见”。异见不仅仅指政治党派或社会伙伴就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它指任何集体处境的给定物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对象化,即它们不再让自己去参与争议、参与到给定世界范围内的争议世界的论辩框架中。这样,异见恰好就指“政治的美学”被解散。
对异见的政治舞台和政治发明的消除或削弱,都对美学的政治产生矛盾的效果。一方面,它给予作为政治实践的艺术实践以新的可见性——我指的是空间与时间、普通物的可见性的形式、事物、图像与意义的联系形式的重新分配的实践。艺术表演可能出现,有时候就出现了,因此,是作为异见舞台建设中的政治替代物。但是,异见并不仅仅让政治空间(politicalplace)放空。它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框定了它的对象的场域。它也用自己的方式形成了艺术实践的空间和任务。例如,它用吸纳与排斥的问题取代阶级冲突的问题,以此表达对“社会契约的丧失”的忧虑、对“赤裸的人性”的关心,或提出任务以授予被威胁的身份以权力来代替政治关怀。艺术于是被召唤去发挥它的政治潜力,以努力去重新框定一种共同体感并修复社会契约。在我看来,从批评范式转向玩笑、收集、邀请和神秘的形式证明了政治性用伦理性的形式进行的重组。
今天的某些项目反对在艺术中用伦理学去代替政治,于是就积极寻找艺术的政治作用。这些都表示了空间的分配问题和处境再描述的问题。它越来越关注传统上属于政治的问题。这个处境就促进了诸多新的努力去让艺术直接地政治性。在最近几年里,许多艺术家都开始复活那种制造真实对象的艺术项目,而不是生产或循环利用图像,或者是在真实世界进行真实行动的艺术项目,而不是仅仅做“艺术的”装置。这样,政治承诺就等于寻找真实。但是,政治性不是艺术必须达到的“真实”的“外围”。“向外”总是“向内”的另一侧。产生其差异的东西是地形学,在它的框架内,协商了进与出的关系。仅仅像这样的“真实”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一种框架或一种现实的虚构。艺术并不是通过获得真实来做政治。它做政治是通过发明诸多虚构去挑战关于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现存分配。
制造虚构并不意味着讲故事,它指的是拆解并重新讲述标识与图像之间、图像与时代之间,或标识与空间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框定了现实的现存感)。虚构发明了新的感知共同体,即可以看到的东西、可以说的东西和可以做的东西之间的新的脉络。它模糊了诸多空间与诸多能力的分配,这也指它模糊了定义其自身的行动的边界;做艺术意味着移动艺术的边界,正如做政治意味着移动被承认为政治性的领域的边界。今天的有些最有趣的艺术品涉及地域和边界就不是巧合的事了。美学的政治中最似是而非的东西可能是:今天的艺术可能通过发明美学距离或美学冷漠的新形式,来帮助框定新的政治的感知共同体,来反对一致同意。艺术不能仅仅占据政治冲突被减弱后留下的空间,它必须重新塑造它,冒着测试它自身政治的底线的危险。
作者 | 雅克·朗西埃,法国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荣誉教授
译者 | 王春辰,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原文发表于《大学与美术馆》总第五期
———————————————————————
注释:
1 雅科托夫人(1778-1855),第一帝国时期最著名的瓷器艺术家。
2 塞索斯特里王即古埃及法老乌斯特桑二世(公元前14-13世纪)。
3 拉图尔(1704-1788),法国著名的彩粉肖像画家。
4 杜巴里夫人(1743-1793),路易十五宠幸的女人,以生活奢侈、行为浪漫著名,大革命时期被送上断头台。
5 奥古斯特大帝(公元前63-公元14世纪),恺撒大帝的侄孙,也是他的继承人,他统治的时期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光荣最繁盛的时期。
6 巴尔扎克:《驴皮记》,北京学苑音像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袁鹏译,第15页。
7 席勒:《人类审美教育书简》,第109页。
8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9 布瑞奥:《关系美学》。